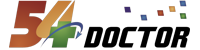院士之思
从女儿角度看“控烟之父”
我和我的先生是79年认识的,我们相识的开始正好是戒烟工作的开始。一天父亲走过来对我的先生说,做我的女婿是不许抽烟的。同时递给我一包东西,打开一看,原来是一件印着戒烟标志的广告衫。我的先生从前当过兵,即刻把广告衫套在身上说:按领导要求办。从此,在戒烟宣传队伍中多了一位高个子宣传员。
当时做戒烟广告是不被认知的。我先生穿着戒烟广告衫上班,经常受到吸烟同事的嘲笑,有的人会故意在他面前吸烟。记得我曾在东大桥的商场里看到挂着“吸烟有害健康”的红色横幅。亲眼见到有两个斜叼着烟卷的年轻人,故意走到横幅前晃悠,脸上带有挑衅的神色。当戒烟宣传员向前劝阻时,他们还讥讽,甚至辱骂。
我为父亲的戒烟工作捏着一把汗。有一天,我看到父亲与两个宣传戒烟积极分子的合影,不禁惊呆了:父亲站在中间,左右两个像小丑的摸样人,头上戴着“卓别林帽子”,帽子上画着五颜六色的戒烟广告,身上穿的衣服也是稀奇古怪的。爸爸解释说,这是两名从全国选出来的戒烟宣传积极分子代表,称为“南怪北狂”,穿戴古怪的原因是要引起社会群众的注意。
其实,父亲大可不必做这样艰难、不被人们理解的戒烟工作。早在1956年,父亲就已经成为《中华内科杂志》副主编,他完全可以仅仅做一名被人尊重的大医生就挺好。
我实在太不理解父亲的戒烟工作!有一次我不禁说出自己担心。父亲的解释让我豁然开朗:正由于我是大内科专家,我才有经验,有资格说:很多不同种类的疾病,例如心血管病、脑卒中、恶性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都与吸烟有关……。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宣布:吸烟是“现代的鼠疫”。我们的国家烟民多达3亿!如果这么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因为吸烟患病,我们的民族不就危险了?我们的国家不就蒙难?爸爸的一席话让我感到震动,我没有想到,不被人看好的戒烟工作却包含着宏图大志的伟业!
有一天,父亲回家来笑嘻地说他今天在市长面前出了“风头”。原来那天他在市人大会上,看到市长在会场上点燃了一支烟,父亲立即写了一张纸条递到主席台,希望市长带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。市长看到纸条后当即把烟掐了。父亲因为这事好像得了个喜帖子,他已经实实在在地把戒烟宣传做到领导的层面上。
虽然,全国戒烟宣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了。但是这样的宣传并没有能得到法律部门的认知。有两名外地戒烟宣传积极分子去逛王府井,看到一张“万宝路”香烟广告居然贴在百货大楼内,是可忍孰不可忍!当他们要采取行动的时候,却被当地的纠察队员扭送到派出所。在派出所里面也有烟民,不由分说把他们两个以“扰乱社会治序”的名义关进了收容所,最终被送回原籍。父亲知道后非常着急,他认识到戒烟工作必须提升到法律层面。他亲自写报告给有关上级部门,强调法律部门也要理解支持戒烟工作。最终,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向这两位戒烟宜传积极分子公开道歉,并给出3963元作为经济赔偿。
只有对全国吸烟人群做科学的调查,才能得出科学的控烟方法。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“吸烟大国”,到底什么人在吸烟?他们开始吸烟的年龄?吸烟的量和种类?所受教育程度如何?等等,了解烟民的详细情况无疑是非常重要的。
50万人口大调查开始启动了。
调査要广泛:除了台湾省以外,29个省市要全部列入调查范围。根据全国人口统计数据,抽取总人口的万分之五比率,对15岁以上人口进行调查。
抽样要科学:各省随机抽取2-3个城市,抽中的城市中随机选定1-2个区,在每个区随机抽取1个街道。最后逐户门询问15岁以上所有家庭成员。
询问要标准:完全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“关于吸烟情况标准化调查方法的建议”来制定询问表格。不然的话,所有的调查工作将失去意义。
毫无疑问,这是一项史无前例、浩大的,既科学又繁难的控烟工程。为了慎重,父亲多次邀请流行病学、统计学等专家共同讨论。先选择2000名北京市的城、乡居民进行预备调查。确认调查的方法切实可行,再由爱卫会和卫生部下发通知,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负责人,到北京参加全国吸烟人群抽样调查学习班。再进一步从各地市县选定调查员,层层办学习班,统一询问方法,理解表格意义,确保结果正确。
调査工作从开办学习班,到入户调查完成,历时七个月。在此期间父亲不停地询问进展细节,确认调查是否合乎要求?反复强调保证调査质量。他要亲眼看,亲自调研,才能及时发现解决问题。他想尽各种方法亲临现场,发现错误,不论別人的还是自己的,都立即及时改正。因为迟到的改正是没有意义的。
1986年初,各地的吸烟人口调查数据汇总到北京,当时的计算机技术还很不成熟,父亲又带领一班人马,坐在冷板凳上埋头于大量的、枯燥的、手抄数据的整理。经过统计,全国调查人口总数是519600人,在这51万人中的平均吸烟率是34.5%,其中20岁以上男性的吸烟率高达70%!45-59岁之间的男性的吸烟比率更高…。这份51万人的调查报告是当时世界上吸烟与健康流行病学调査报告中,调查人口最多、地域最广、耗时最久、统计数据最全面、最精准的吸烟情况文献资料。它填补了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,具有国际领先水平。为制定我国的控烟战略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可靠数据。
对父亲来说,这份调查报告也表明,从那时候开始,他真正的掌握了中国的吸烟情况,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控制吸烟运动的领导者。
51万人的大调查完成了,然而父亲等备多年的“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”还没有成立。建立国家层面的组织,才是解决“控烟”的有效策略。父亲几次联合其他业内的专家发出《加强控制吸烟倡议书》,希望得到中国科协批准。但是中国科协认为没有权利批准这样的组织成立,应该请国务院来决定。而国务院是从来不审批非行政组织的。
父亲看惯了类似的“打太极”,这个结果也在他的想象中。他不气缓,利用自己是北京人大代表、北京市科协常委等身份,不厌其烦地交倡议书,向决策者游说。在他真诚恳切,持之以恒的提议下,中国第一个吸烟与健康协会——北京市吸烟与健康协会于1987年5月宣告成立。
父亲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吸烟与健康的论文20余篇。其中有一篇名为《控制吸烟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强壮、昌盛的大事》。文章指出:来自烟草的利税,远远抵偿不了由吸烟造成的巨大损失。吸烟的危害昭然若揭,为什么有令不行,收效甚微呢?他分析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:国家从烟草产品中所获利税收太大;以及相关决策人员有吸烟习惯,对控烟运动不积极。……国家决策层应该从中华名族强壮、昌盛的长远利益着眼,深谋远虑,如果再不控烟,后果将不堪想象。
1990年2月,反对吸烟的志士仁人们有理有据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成果。经卫生部和民政部联合批准,中国吸烟与健康协会终于宣告成立了!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阶平先生任会长,父亲任常务副会长。
1991年,协会成立第二年,吴阶平先生高兴地宜布:《吸烟危害控制法》开始讨论了!全国吸烟与健康学术研讨会要举办了!与《健康报》联合开办“吸烟与健康”专题栏目要登出了!……好消息连连。又据《中国吸烟与健康通讯》报道,近90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毅然戒烟了;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都一致与香烟说“拜拜”了。1993年9月国务院宣布,同意申办1997年第十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。
第十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能不能如愿在北京召开是个谜。因务院交给的这个申办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父亲的身上。父亲深知,这是他一生中重要的使命。当时申办会议举办国不仅仅有中国,还有芬兰,土耳其,葡萄牙三国也在申办。这三个国家虽然不大,但是对控烟己经做出很多成绩。例如北欧小国芬兰,在1976年就通过了烟草法令,规定烟草税收的一部分必须用在反对吸烟的活动中。再说土耳其,1988年就有67个省制定了禁烟章程;土耳其卫生部长带头,在电视中集体演出一个节目:“最后一支烟”。所以,中国要获得第十届大会的主办权,并无太大胜算。
1994年10月9日,第九届世界吸烟与健康大会在巴黎召开。父亲代表中国亲自登台,用流利的英语向世界阐述: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,也是烟草产、销量最大的国家。烟民多达3亿,占世界吸烟人数的1/4。中国政府领导人已经意识到烟草的危害,把控烟作为一种责任。……我们面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,所以我们很希望可以得到全世界同行人士的声援和支持。…-我们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,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国的控烟工作。到世界上产烟最大、烟民最多的中国举行大会,毫无疑问,必将强劲地推动中国和世界的控烟运动;从长远的眼光看,肯定不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,而且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在大会闭幕式上,主持人宣布:第十届世界控烟大会定于1997年8月24日在北京召开
这时候,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,祝贺中国代表团申办成功。父亲这时候深深地舒了一口气,他累了,他心中不由产生“不辱使命”的欣慰之情。
那年,父亲75岁。后来,他一直在控烟岗位上工作直到干不动为止。这就是我的父亲,控烟之父——翁心植先生。
(翁维馨)